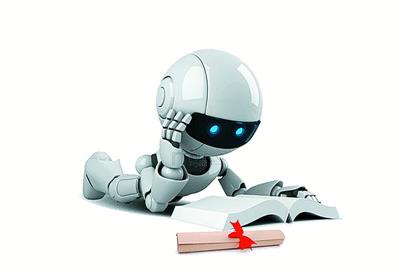
《死在南方》以科幻的笔法构造了一个人类大灭绝时代。以“我”的第一视角阐述故事情节,意旨深远,读来令人产生许多关于机械领域发展,地球时间的归属和离散、人性思维的渗透、人类命运走向的思考,在科幻中映射现实,奇异中散发着辩证性哲思。
一、第一叙述视角的审视
“我”的第一叙述视角贴合科幻背景,以科幻的记录性视角映射真实的地球。“在南方,我和M是盗墓机器人”,开篇便已设定了冰冷的记述视角,表明了“盗墓机器人”的身份定位。引人思索:为何是强调在南方?如何盗墓?为何盗墓?盗何人的墓?下文一一以冰冷的视角与口吻给予回应。“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我们的劳动为何被称为盗墓,而不是挖坟,毕竟人类已经灭绝。”“也许”“也许”是“我”的不解与不屑,“我”和M是按既定程序“劳动”,尽显对待死亡、生命的凝视与冰冷。
警示与沉痛的语言是我们在科幻场景中对于地球现状的真实叩问。“人类经历了一场惨不忍睹的战争,他们自爆了。他们可谓破坏之王,我们去过好几个存在过生命的星球,没有见到过被破坏成这样的。”我们以讽刺性的沉痛语言,警醒世人,人类面临死亡是脆弱的。“享受”一词以反语的表述直击灵魂,曾经美丽的蓝色星球,如今却已是满目疮痍,其中传达出的警示和痛心是沉重的。警示与沉痛并存的语言赋予了小说更深层次的生命主题,将地球的命运,人类的生存,族群的延续,机械发展等领域都交织一起,等待后来人思索真实的世界。
二、时空转换的真实映射
小说以小标题形式推动故事发展,逐步升华主题。时间概念已然模糊,人类已经灭绝好些年,将现实拉回到那些被生物元素侵占人类印记场景中,“我”和M不知在地球劳动了多久,只好用一些标志性的事物来记录。而公交车是人类遗留在地球的可运转的重要的唯一的便利,他们按照固定的路线,不知走了多少年,宇宙混沌以及时间的模糊尽然体现在这机械的物体上,连同下文出现的机械蛙和机械蛇也不知在地下埋藏了多长时间。公交车是带我们离开既定程序的工具载体,南方公园是旅行的终点,也是故事情节发生波澜的转折地,在这里我们又开始新一轮的工作,也由此产生了俱乐部是否已将我们遗忘或重新分配了劳动任务的思考。牙齿的出现为我们带来新的方向,牙齿的主人显然与其他人们不一样,当人类主人还活着时,地球还是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星球,似乎我们长时间的盗墓出现了转机与希望,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为下文我和M深入挖掘做了铺垫,也为下文机械蛙、机械蛇和头盖骨的出现埋下伏笔,为挖掘荒诞背后的现实蓄力。
小标题助力场景切换,呼唤纯真人性。南方是限定场景,公交车永不止步,带着我们穿过河流,将我们带到了南方公园,南方多雨,雨过后又是炙热的太阳,植物的生长快速,人类文明痕迹也在南方的环境中逐渐被侵占掩盖。荒芜、奇异、寂静是固定的大环境,破败不堪的公交车,南方公园的断墙残垣都渗透出惊悚感。一切又似乎回归人类诞生之前,杂草、大树都在为自己独享这片大地而欢呼,野蛮生长的他们将狼藉的地表遮盖住了,同时又昭示着地球蕴藏无限生机。牙齿和坚硬的头盖骨是我们在非正常死亡的人类族群中苦苦寻觅许久,耗费了一番心血才找到的。这映射出人类的生存现状不容乐观,人类只是暂住者,地球将会以新的环境孕育生命活力。
三、人类思维的挣扎与闪现
如果说南越王赵佗的头盖骨被复活,最终看到自己的非人的机械身体而毁灭自我,是对“非人”处境的批判,是人类思维的体现,那么,机器人本身若隐若现的对程序的叛逆与质疑,则更是人类思维的体现。“我”与M的设定是机器人,不知何人所造,只知来自于机器人俱乐部,身体也被导入盗墓代码。我们的一切行为活动都源于被编入的代码程序。诚然,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M都无法理解许多事,比如人类为何会死亡,不知为何我们要盗墓,感情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范畴,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都产生了程序代码以外的行为和情感。带有浓烈人性色彩的举动,昭示着机械人与人类思维的碰撞与融合,人类的影子仍然存在。程序代码的冰冷死板与人类思维的灵活丰富产生了碰撞和交融。最后,人性思维的突破矛盾的束缚,点亮机械生命的光辉。
四、生命走向的真实拷问
小说以机器人视角展示了人类自己无法延续族群而导致大灭绝的现实,以科幻笔法揭示了人类生存的真实困境。这是对人类的真实拷问:人类终将是地球的过客吗?是否有地球之外的生命存在?利用头盖骨和牙齿呈现人类文明,省略的是人类文明是否得以重现的猜测与希冀,也可能省略的是人类文明重蹈覆辙的悲剧。梁宝星以奇异、诡谲的文字引发人类读者思考审视自身,试图点醒梦中人。部分科幻笔法基于科学领域的真实支撑,真实世界又将这部分映照在科幻成分中,在科幻中追寻真实,真实中审视科幻,人类之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文明延续的追问持续不断。帝王将相之墓,坚硬的头骨和牙齿给这段长时间的盗墓画上了一个短暂的句号。下一工作任务的开启又给重现人类文明带来了希望,故事设置了悬念,给这颗沉寂已久的星球留下了鲜活的希望种子。
科幻的种子,开出奇异之花,真实的土壤,孕育生命之花。
(科幻小说《死在南方》 发表于《长城》2023年第5期 作者系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语文教师)
